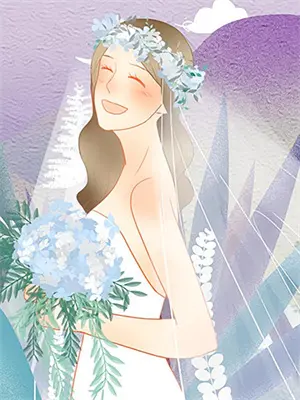
苏糯第三次把裱花袋重重摔在操作台上时,奶油溅到了天花板上,像朵歪歪扭扭的云。
“又废了。”她盯着蛋糕胚上那坨不成形的奶油,气鼓鼓地踢了踢脚下的防滑垫。淡粉色的奶油顺着蛋糕边缘往下淌,活像只被踩扁的草莓,黏糊糊地挂在侧面,与她设想中“层叠如花瓣”的效果相去甚远。
烘焙坊的玻璃门“叮咚”一声被推开,风铃摇晃着撞出细碎的响。苏糯没回头,只听见熟悉的、带着点户外阳光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——是陆屿。
“又跟奶油置气?”他的声音里裹着笑,带着刚跑完外勤的微喘。苏糯转身时,正看见他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,军绿色的冲锋衣拉链敞开着,露出里面印着相机图案的白T恤,领口沾着点草屑,像是刚从郊外回来。
“它不听话。”苏糯指着蛋糕,语气委屈得像个被抢了糖的孩子,“你看这奶油,软塌塌的,根本立不起来。师傅说再练不好裱花,就让我去做面包了,可我不想揉面团,手会酸。”
陆屿放下肩上的摄影包,包带在他锁骨处勒出浅浅的红痕。他俯身凑近蛋糕,指尖轻轻碰了下奶油,又缩回来,在阳光下捻了捻:“温度太高了。你把空调再调低两度,奶油硬度够了,自然能立住。”他说话时,呼吸扫过苏糯的耳廓,带着点薄荷糖的清凉——是他常吃的那种,说是拍外景时含着提神。
苏糯脸颊发烫,转身去调空调,嘴里嘟囔着“早不说”,心里却把这句话刻进了备忘录。她知道陆屿懂这些,他姐姐开了家甜品店,他耳濡目染,比烘焙坊的老师傅还清楚奶油的脾气。
等她回来时,陆屿已经拿起裱花袋,舀了点新打发的奶油。他站在操作台旁,左手扶着蛋糕转台,右手手腕轻转,淡粉色的奶油在他指尖乖乖听话,一圈圈叠成半开的花苞。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他手上,能看见他指腹上的薄茧——是常年握相机磨出来的,此刻却灵活得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。
“看好了。”他头也不抬,声音低沉,“裱花袋要捏稳,但别用力死攥,就像……就像你拿画笔描边,力道匀了才好看。”
苏糯盯着他的手,忽然发现他食指第二节有个小小的疤痕,像道浅粉色的月牙。她以前没注意过,此刻看得入了神,连他什么时候停下的都没察觉。
“喂,看傻了?”陆屿屈起手指,敲了敲她的额头,“该你了。”
她接过裱花袋时,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,像触到团温热的棉花,麻酥酥的电流顺着手臂窜到心口。苏糯深吸一口气,学着他的样子调整姿势,手腕刚转半圈,奶油就不听话地“啪嗒”掉在蛋糕上,砸出个丑丑的坑。
“笨蛋。”陆屿笑着拿过纸巾,替她擦掉手上沾的奶油,“别盯着奶油看,看转台。你要让蛋糕跟着你的节奏转,不是你被它带着跑。”他的指尖偶尔擦过她的手背,像片羽毛轻轻扫过,苏糯的心跳突然乱了节拍,连呼吸都忘了调整。
就这样练了整整一下午,直到夕阳把操作台染成橘红色,苏糯才勉强挤出一朵像样的玫瑰。花瓣歪歪扭扭,边缘还有点焦是她不小心碰倒了旁边的烤箱按钮,但总算立住了。
“进步很大。”陆屿举起挂在脖子上的微单,对着蛋糕“咔嚓”拍了张照。相机屏幕亮起时,苏糯看见他把照片设成了屏保——之前的屏保是片云海,据说是他在海拔四千米的山上拍的。
“你怎么总拍这些?”她凑过去看,鼻尖差点碰到他的肩膀,“拍风景不好吗?”
“风景哪有你好玩。”他说得坦然,手指在屏幕上滑动,调出另一张照片——是上周她蹲在地上捡碎掉的曲奇,头发乱糟糟的,嘴角还沾着点巧克力酱。苏糯“呀”了一声,伸手去抢相机,却被他举过头顶。
“还给我!删掉!”她跳起来够,帆布鞋在防滑垫上蹭出“沙沙”的响,阳光从他身后涌过来,给他周身镀了层金边,连汗湿的发梢都亮晶晶的。
“不删。”陆屿笑着后退,撞到了身后的原料架,一袋低筋面粉“哗啦”掉下来,白花花地撒了他一身。苏糯愣了两秒,突然笑出声,看着他像只刚滚过雪地的小熊,连睫毛上都沾着粉。
“还笑?”陆屿挑眉,伸手抹了把脸,反倒把面粉抹得更匀,“再笑我就把这张也存进去,命名为‘笨蛋裱花师的日常’。”
苏糯赶紧捂住嘴,却在他转身去拿扫帚时,偷偷拿起他的微单。屏幕还亮着,她点开相册,发现里面藏着好多自己的照片:有她趴在操作台上打盹的,有她举着刚出炉的牛角包傻笑的,还有张是她被烤箱烫到手指,龇牙咧嘴吹手的样子。每张照片的角度都很温柔,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,连她额前乱翘的碎发都拍得清清楚楚。
“偷看什么呢?”陆屿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,苏糯手忙脚乱地把相机塞回去,脸颊比刚打发的奶油还烫。他没追问,只是拿起毛巾擦了擦身上的面粉,轻声说:“下周我要去邻市拍湿地,大概三天。”
“哦。”苏糯低下头,假装整理裱花袋,心里却有点空落落的。
“给你留了东西。”陆屿指了指他的摄影包,“在侧袋里。”说完,他转身去清理地上的面粉,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,像在数着什么。
苏糯拉开他的侧袋,摸到个硬纸筒,抽出来一看,是卷崭新的烘焙油纸,包装上画着片星空,每颗星星旁边都标着日期——是她开始学裱花的日子。纸筒里还藏着张便签,字迹清隽:“奶油最佳温度18℃,裱花袋要捏在三分之一处,转台转速调慢档。我问过姐姐了,她教的。”
窗外的风铃又响了,这次是被晚风吹的。苏糯捏着便签,看着陆屿弯腰扫地的背影,突然觉得那些难搞的奶油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。她走到他身边,递过一张湿纸巾:“喏,擦脸。”
陆屿接过时,指尖又碰到了她的,这次没像之前那样躲开。两人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,在满地面粉上重叠在一起,像幅没画完的素描。
“对了,”苏糯突然想起什么,“你拍湿地要带长焦镜头吗?我听师傅说那边的芦苇很高,说不定会挡住视线。”
带了70-200mm的。”陆屿笑了,“放心,拍得到水鸟。”他顿了顿,补充道,“我会每天给你发照片的,湿地的晚霞很好看,比烘焙坊的灯光好看。”
苏糯“嗯”了一声,看着他把摄影包重新背上,看着他推门时风铃再次摇晃,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街角的梧桐树下。直到玻璃门缓缓合上,她才低头看向那张便签,突然发现背面还有行小字:“等我回来,教你做奶油霜,比这个好裱多了。”
操作台上,那朵歪歪扭扭的玫瑰还立在蛋糕上,淡粉色的奶油在晚风中微微晃动,像在点头应着什么。苏糯拿起裱花袋,对着空气又试了一次,这次的弧度好像比之前顺了点。
也许,裱花和等待一样,急不得。她想。就像陆屿镜头里的照片,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,要等光,等风,等那个恰好的瞬间。
晚上关店时,苏糯把那张星空油纸铺在操作台上,对着月光练习转手腕。奶油在纸上画出弯弯的弧线,像条银色的河。她拿出手机,给陆屿发了条消息:“路上小心,拍晚霞时别站太近水边。”
没过多久,手机震了震,是他的回复,附带一张照片——是烘焙坊的玻璃窗,她的侧影映在里面,正专注地盯着裱花袋,窗外的月亮刚好落在她肩头。
“刚拍的。”他说,“你认真的样子,比晚霞好看。”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