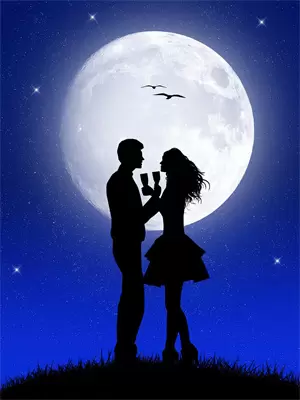大伯娘把我丢給了收破烂的老王,家被我爸掀了暴雨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地上,
泥泞的巷口泛着浑浊的光。大伯娘攥着我的手腕,指甲几乎嵌进肉里,
她脸上堆着从未有过的慌乱,呼吸都带着急促的喘息。收破烂的老王正弯腰捆扎废品,
三轮车上的塑料瓶叮当作响。“这孩子没人要了,你带着给口饭吃就行!
” 大伯娘的声音尖利又含糊,不等老王反应,就猛地将我往前一推。
我重重摔在三轮车的铁板上,冰凉的雨水瞬间浸透单薄的衣衫。“大伯娘!
” 我撕心裂肺地哭喊,伸手想抓住她的衣角,可她转身就冲进雨幕,身影很快消失在巷尾。
老王愣在原地,手里的绳子滑落在地,我蜷缩在废品堆旁,看着陌生的昏暗巷口,
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不解。1 家中的异类我们家窝在老城区最深处的窄巷里,
青石板路被几十年的脚步磨得发亮,一到梅雨季就沁出湿漉漉的潮气,
混着隔壁酱菜铺的咸香和巷口公厕的异味,黏在人衣服上甩都甩不掉。
两侧的青砖灰瓦挤得密不透风,房檐压得很低,阳光只有正午时分才能勉强斜着切进来,
在墙根投下一小片转瞬即逝的亮斑。我们家那栋两层小楼更是局促,
木楼梯踩上去“吱呀”乱响,楼上说话楼下听得一清二楚,连咳嗽都得捂着嘴,
生怕惊扰了一墙之隔的爷爷奶奶。父亲林建军就住在这样的地方,
却像株错栽在瓦缝里的白杨树,浑身上下透着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清爽。
他是林家兄弟姐妹里唯一身高过一米八的,肩宽腰窄,
不像大伯二伯那样被常年的体力活催得膀大腰圆、满脸横肉,连脖颈都透着股紧实的线条。
他的眉眼生得周正,鼻梁高挺,眼窝比寻常人略深些,笑起来时眼角会漾出浅浅的纹路,
不像爷爷那样动辄吹胡子瞪眼,更不像大伯那样一开口就带着市井的蛮横,
连说话的语调都比旁人温和,像巷口老井的水,清润不燥。每到傍晚父亲下班回来,
推着那辆擦得锃亮的永久自行车走进巷口时,总能引得家家户户的窗帘动一动。
酱菜铺的老板娘会探出头喊:“建军回来啦?今天气色真好!
”连收水费的大妈都要多跟他说两句。这时候奶奶就坐在堂屋的竹椅上,手里捏着针线,
眼睛却黏在父亲身上,等他走进门,才慢悠悠地对着里屋的姑姑们嘀咕:“你看建军这模样,
真不像咱林家的种,倒像是从哪个大户人家抱来的。”姑姑们就凑过来,手指绞着围裙,
语气里藏着说不清的羡慕和疏离。大姑扒着门框往巷口瞥,压低声音:“上次我去菜市场,
卖鱼的老板还问我,这是你家雇的帮工?说长得比电影里的明星还精神。
”小姑就撇嘴:“长得好有啥用?还不是每月工资都得上交一半。”爷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,
烟杆在鞋底敲得“笃笃”响,听见了就闷哼一声打断:“长得好能当饭吃?
挣钱养家才是本事。”可话虽如此,家里但凡有对外的事,比如给爷爷办寿宴订馆子,
或是跟邻居闹了纠纷要调解,爷爷还是会下意识拍桌子喊:“让建军去!他模样周正,
说话体面。”最先把这份“体面”当成猎物的,是大伯娘李秀莲。她嫁给大伯前,
是巷尾裁缝铺的学徒,脸盘圆,腰也粗,说话像打锣,一开口就带着股咋咋呼呼的劲儿。
那时候她总借着送缝好的衣服为由头往我们家跑,每次都恰逢父亲在家。
有次父亲帮隔壁张大爷修自行车,蹲在院子里卸链条,阳光落在他汗湿的额发上,
泛着浅金色的光。李秀莲就站在院门口的石榴树下,手里的碎布掉在地上都没察觉,
眼睛直勾勾地黏在父亲身上。直到家里人在巷口喊她回家吃饭,才猛地回过神,脸涨得通红,
慌慌张张地捡了布就跑,连句招呼都忘了打。后来她嫁给大伯,婚宴就摆在巷口的小饭馆里,
油腻的圆桌擦得发亮,盘子里的红烧肉堆得冒尖。她喝了点酒,
红着眼圈拉着父亲的胳膊不肯放,指甲几乎要嵌进父亲的袖口:“建军弟,
你咋就不看看我呢?我哪儿比不上别人?我能给你洗衣做饭,
能伺候爹妈……”父亲当时就皱了眉,不动声色地抽回胳膊,
指尖都染上了她身上廉价雪花膏的味道。奶奶正好端着汤过来,看见这一幕,
只笑着打圆场:“秀莲喝多了,胡言乱语呢,建军你别往心里去。
”婚后的李秀莲更是变本加厉,借着“一家人”的由头,把父亲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。
父亲下班刚推开门,她总能“恰巧”端着一碗刚煮好的糖水从厨房钻出来,碗沿还冒着热气,
非要看着父亲一口一口喝下去才肯走,那眼神热得像要把人烧穿。父亲的工作服脏了,
她抢在我妈前面抱走,洗的时候故意用香精皂,晾在二楼的竹竿上,
把自己的花衬衫和父亲的蓝布褂子紧紧挨在一起,风一吹就蹭来蹭去。
最过分的是有一年秋天,父亲感冒发烧躺在床上,额头烧得滚烫。半夜我被尿憋醒,
听见堂屋有动静,扒着门缝一看,李秀莲正端着退烧药走进父亲的房间,
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,伸手就要摸父亲的额头。父亲猛地从床上坐起来,侧身躲开,
声音沙哑却带着寒意:“嫂子,男女有别,你出去。”李秀莲的手僵在半空,
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好半天才讪讪地把药放在床头柜上,嘴里嘟囔着“好心没好报”,
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,路过我门口时,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这些腌臜事,
家里人都看在眼里,却各有各的心思。大伯每天早出晚归跑运输,要么假装没看见,
要么被李秀莲几句“我都是为了这个家”的甜言蜜语哄得团团转,
还总拍着父亲的肩膀说:“我媳妇就是热心肠,疼弟弟比疼我还甚。”我妈抱着我坐在床沿,
手指绞着床单,眼圈红红的,却只能压低声音跟父亲说:“你离她远点儿,免得被人说闲话。
”父亲靠在床头抽烟,烟圈一圈圈飘向屋顶的蛛网,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,
一边恼怒李秀莲的得寸进尺,一边又怕爷爷奶奶骂他“不识好歹”,
更怕传出去影响兄弟和气,只能一次次忍着,下班回来就躲进房间,连堂屋都很少去。
2 爸妈的婚姻父亲和母亲的婚事,是巷子里那年最体面的一桩。母亲是父亲初中同学,
在纺织厂当女工,眉眼清秀,性子温软却有主见,
早在上学时就悄悄把父亲写的运动会加油稿夹在课本里。两人确定关系后,母亲第一次上门,
就把李秀莲递来的“试探性”糖水轻轻推到一边,笑着说:“建军不爱吃甜的,
我带了他喜欢的薄荷糖。”那语气不卑不亢,倒让李秀莲的脸僵了半天。婚后的日子,
挤在二楼那间仅十平米的小屋里,却处处透着甜。父亲每天下班,
自行车筐里总藏着惊喜——有时是母亲爱吃的糖糕,有时是几支路边采的野菊,
插在旧墨水瓶里,能香满整个小屋。母亲则把小窝打理得井井有条,
父亲的蓝布褂子永远浆洗得笔挺,领口缝着细密的针脚;晚上父亲伏案学电工知识,
母亲就坐在一旁纳鞋底,台灯的光晕落在两人发顶,连木楼板的“吱呀”声都变得温柔。
最让他们盼头十足的,是攒钱租房单过的念头。母亲特意买了个带锁的铁皮盒,每次发工资,
两人就凑在一起数钱,硬币撞得“叮当”响。“巷口那间刚空出来的小平房就挺好,
”母亲指着窗外,眼睛亮得像星星,“有个小院子,能种点青菜,晚上咱们能安安静静说话,
不用总怕吵着老人。”父亲攥着她的手,指尖划过她掌心的薄茧:“再攒三个月,
咱们就去谈房租,到时候给你买个新的缝纫机,放窗边,采光好。
”可这念头刚在饭桌上说出口,就像往滚油里泼了瓢冷水。爷爷正扒着饭,
筷子“啪”地拍在桌上,米粒溅了一桌子:“单过?翅膀硬了是不是?我还没死呢,
你就想分家?”奶奶放下碗,抹起了眼泪,声音颤巍巍的:“建军啊,你忘了小时候发烧,
是谁整夜抱着你去医院?现在娶了媳妇,就不要爹妈了?咱们林家祖祖辈辈都没分家的规矩,
你这是要让街坊邻居戳我脊梁骨啊!”父亲刚要解释,大伯就抢先开口:“弟,
不是当哥的说你,一家人住一起多热闹,有个头疼脑热的也有个照应。再说,爹妈年纪大了,
就盼着儿孙绕膝,你咋这么不懂事?”李秀莲在一旁煽风点火,
往爷爷碗里夹了块肉:“爸您别气,建军就是被媳妇迷了心窍。这刚结婚就想单过,
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是咱老林家待不住新媳妇呢。”只有小姑私下里溜进我们房间,
蹲在我妈身边抱怨:“嫂子,你可得看紧我哥,秀莲那眼神,跟饿狼似的,不对劲得很。
”她手里攥着个刚从树上摘的橘子,剥得汁水淋漓,“上次我看见她偷偷翻我哥的抽屉,
不知道在找啥。”可抱怨归抱怨,她转头遇见李秀莲,还是会笑着喊“嫂子”,
在这个把“家和万事兴”挂在嘴边的老房子里,没人愿意撕破脸。
墙缝里的潮气一点点渗进来,像那些藏在暗处的心思,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这栋拥挤的小楼,
只等着一个契机,就彻底崩塌。母亲脸色发白,攥着筷子的手微微发抖,
却还是轻声说:“爸妈,我们不是要分家,就是想有个自己的小空间,房租我们自己付,
每月该给的生活费一分都不会少。”“生活费?”爷爷冷笑一声,“你那点工资够干啥?
建军每月工资上交一半,这是规矩!你们租房不要钱?买家具不要钱?到时候钱不够,
还不是要往家里伸手?”接下来几天,家里彻底没了安宁。
奶奶每天坐在父亲房门口哭哭啼啼,
翻来覆去说当年的养育之恩;爷爷则找来了家族里的老叔公,让他对着父亲训话,
说他“不孝”“忘本”。更狠的是,发薪日那天,爷爷直接让大伯去父亲单位,
以“家里急用”为由,把父亲的工资领走了大半。3 恶意与被弃租房的事黄了以后,
大伯娘李秀莲看我们娘俩的眼神,就像淬了毒的钢针,扎得人后背发僵。
她的嫉妒从来都摆不上台面,却又无孔不入——嫉妒母亲总能在父亲晚归时,
收到带着体温的烤红薯;嫉妒父亲会蹲在小板凳上,
耐心给我梳歪扭的辫子;甚至嫉妒我摔碎了碗,父亲皱眉说的是“没扎到手吧”,
而不是像对她那样,劈头盖脸一句“毛手毛脚”。这份不甘在她心里熬成了黑汤,
连行为都变得怪异起来。她开始故意在我面前摔东西,洗碗时“哐当”一声把瓷碗磕在池边,
盯着我冷笑:“有的丫头就是讨债鬼,耗得大人不得安宁。”母亲织给我的毛衣,
隔天就会出现个破洞,她说是“被老鼠咬的”,可我分明看见她藏在背后的剪刀尖沾着毛线。
更龌龊的是,她总在巷口跟邻居嚼舌根,说母亲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,
连生个丫头都娇贵得像公主,暗指我是拖累林家的赔钱货。压垮她理智的,
是父亲给我买的那只布娃娃。那天是我的五岁生日,父亲攥着攒了半个月的零钱,
从百货商店给我抱回个穿花裙子的娃娃,眼睛是黑亮的玻璃珠,笑起来嘴角还有个小梨涡。
我抱着娃娃在院子里转圈,不小心撞翻了她端来的洗衣盆,肥皂水溅了她一裤腿。
我吓得赶紧道歉,她却突然不骂了,蹲下来盯着我的娃娃,
手指捏得咯咯响:“丫丫这娃娃真好看,比你妈当年的嫁妆还金贵。
”当晚我就听见她跟大伯在房里吵架,摔杯子的声音震得楼板都颤:“他林建军眼里有谁?
工资上交一半是给老的,剩下的全填了那娘俩的窟窿!我嫁进林家三年,
他给我买过一根针吗?”大伯闷头抽烟,只会说“你别胡搅蛮缠”。后来我才知道,
那天她跟父亲要块花布做头巾,被父亲以“家里钱紧”拒绝了,转头父亲就给我买了布娃娃。
从那天起,她看我的眼神里,就多了种猎物入笼的阴狠。事发在一个周六的清晨,
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,风卷着沙尘往人眼里钻。母亲要去纺织厂加班,
临走前给我梳了两条小辫,塞了块玉米饼在我手里:“乖乖在家写数字,爸妈中午就回来。
”父亲要去城郊修电路,特意把我的布娃娃放在床头:“抱着娃娃等爸爸,别给陌生人开门。
”可我刚趴在桌上写了三个“1”,李秀莲就挎着菜篮子推门进来,脸上堆着从没有过的笑,
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。“丫丫乖,”她从口袋里掏出颗用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,
糖纸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彩光,“你妈刚才托人带话,说巷口新来了个卖糖人的,
让我带你去挑个孙悟空,给你爸一个惊喜。”我摇摇头,记着父亲的话:“我不去,
等爸妈回来。”她立马蹲下来,把糖塞进我手里,粗糙的拇指摩挲着我的手背,
语气软得像棉花:“傻丫头,你妈说买完就带你回来。你看这糖,是橘子味的,
比你上次吃的奶糖还甜。”她又指了指门外,“你听,是不是有吹糖人的声音?
再不去就被别的小孩抢光了。”我捏着那颗发烫的糖,
听见远处隐约传来“嗡隆嗡隆”的声响,肚子里的馋虫也开始叫了。她趁机拉起我的手,
力气大得惊人,指甲几乎要嵌进我肉里:“走,嫂子带你去,保证不耽误你等爸妈。
”巷子里静得可怕,平时热闹的早点铺都关着门,只有风卷着落叶滚过青石板路。
我越走越慌,脚下的布鞋磨得脚疼:“大伯娘,我想回家。”她回头瞪了我一眼,
声音突然冷了:“再哭糖人就没了!”我吓得赶紧闭嘴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
手里的糖纸都被攥皱了。走到巷尾的岔路口时,我看见收破烂的老王正蹲在地上捆废纸壳,
他的三轮车堆得像座小山,散发着霉味和废铁的锈味。老王看见我们,抬起头笑了笑,
露出两颗发黄的牙:“李嫂子,带丫头出来玩啊?”李秀莲没理他,突然松开我的手,
快步走到老王身边,声音又尖又急,像被踩了尾巴的猫:“老王,这孩子没人要了,
你带着吧!给口剩饭就行,不占地方!”老王手里的绳子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
眼睛瞪得溜圆:“李嫂子,你疯了?这是建军的丫头!”我还没反应过来,
李秀莲突然转过身,双手猛地推在我肩膀上。我踉跄着往后退,膝盖磕在三轮车的铁板上,
疼得我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“大伯娘!”我伸出手想抓她的衣角,
可她像躲瘟疫似的往后跳,高跟鞋踩在石子上差点摔跤。“别叫我!”她的脸涨得通红,
头发都乱了,眼神里全是疯狂的解脱,“你爹妈根本不想要你!他们嫌你累赘,
让我把你送走!”说完她转身就跑,裙摆扫过路边的野草,跑出去几步还回头看了一眼,
那眼神像淬了毒,看得我浑身发冷。我趴在三轮车边大哭,喊着“爸爸”“妈妈”,
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。老王赶紧把我抱起来,他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,
却轻轻拍着我的背:“丫丫别哭,你大伯娘胡说八道。叔这就带你去找爸妈。
”他刚要发动三轮车,天上突然掉起了雨点,豆大的雨点砸在车棚上“噼啪”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