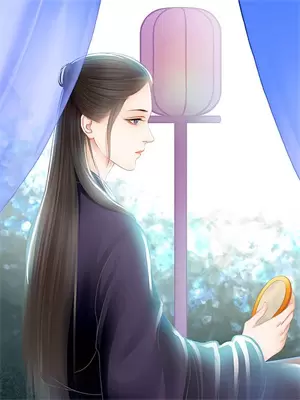第1章子时的琉璃瓦上凝着霜。我蹲在屋顶,手指冻得发麻。数到第七颗流星划过时,
铜环叩门声突然刺破寂静。灯笼在风里晃。光晕边缘站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,
肩上落着未化的雪。他抬手时,我看见罗盘在他掌心结出蛛网状的冰晶。"沈家小子?
"他声音像生锈的刀刮过磨石,"陈青囊。"祖父咽气那晚的画面突然撞进来。
老人枯瘦的手指掐进我腕骨,喉间咕噜着"地脉伤龙"四个字。
铜臭味混着药渣味从记忆里漫上来,我打了个寒颤。门轴吱呀响。引他穿过回廊时,
青砖缝里渗出潮湿的土腥气。灯笼照不到的暗处,所有影子都朝着西墙假山方向歪斜,
像被什么拽着脖子。陈青囊的靴底碾过枯叶。他腰间包袱突然亮起蓝光,
布料下凸出纵横交错的纹路。我假装没看见,他却突然回头:"你祖父没教过你?
活人的影子不该有分量。"假山石洞里传来碎瓷声。我们冲过去时,只看见福伯佝偻的背影。
聋哑老人正把铜钱排成北斗状,听见脚步声,慌忙用鞋底抹乱了图案。"寅时三刻。
"陈青囊蹲下来捡起半枚铜钱,"他要镇的不是煞,是病。"后罩房突然亮起灯。
齐明月白大褂下露出猩红睡裙边角,医药箱挂在她腕间晃荡。她盯着陈青囊包袱里透出的光,
嘴唇抿成直线:"尸厥症患者需要安静。"陈青囊笑了。他从袖中抖出三枚锈钉,
钉尖正指着齐明月药箱暗格:"朱砂画符治不好龙咳。"我后背抵上冰凉的影壁。
齐明月药箱里传来纸张摩擦声,福伯的铜钱在砖缝间微微震颤。
陈青囊包袱上的蓝光突然暴涨,
照亮回廊梁柱上褪色的符咒——那是我七岁时跟着祖父画的镇宅符。瓦片突然哗啦响。
我们抬头时,正看见最后半片流星坠向假山方向,在夜空中拖出病态的绿色尾焰。
第2章雨丝突然变密了。陈青囊的包袱在暗处发着青光,像裹了只萤火虫。他蹲下来,
指甲抠进砖缝,带出几缕暗红色的泥。“看清楚了。”他抹开那些泥,
指腹上沾着细碎的金点,“龙血纹。”我凑近时闻到铁锈味。那些金点在他皮肤下流动,
像活的。假山后传来枯枝断裂声,齐明月的高跟鞋踩在水洼里,
溅起的泥点沾在她白大褂下摆。“退烧药。”她把铝盒扔给我,银针筒在口袋里露出尖头,
“三小时一次。”陈青囊突然抓住她手腕。银针筒掉在地上,针尖自己转向后院。
我们三个都听见了——枯井方向传来沙沙响,像蛇在蜕皮。齐明月弯腰捡针筒,
领口滑出半张黄符。陈青囊吹了声口哨,符纸上的朱砂突然晕开,变成血滴的形状。
“医师也信这个?”他笑得露出虎牙。后院传来铜钱碰撞声。福伯跪在井台边,
正把五帝钱排成奇怪的图案。月光照下来,那些铜钱组成的线条像长了角的龙。亢宿,
我脑子里突然蹦出这个词。“福伯!”我喊他。老人聋了三十年,此刻却猛地回头。
他嘴角挂着黑乎乎的药渣,手里铜钱叮当落了一地。陈青囊的包袱突然剧烈鼓动。
蓝光透过布料,在地上投出纵横交错的影子,像张网。齐明月退后半步,药箱暗格啪地弹开,
露出里面一叠画到一半的符纸。“你们听。”我嗓子发紧。沙沙声变成了刮擦声。
井沿的青苔在月光下诡异地卷边,像被看不见的舌头舔过。陈青囊摸出三枚锈钉,
突然扎进自己掌心。血滴在砖上,立刻被吸干了。“龙咳。”他舔掉掌心的血,“听见没?
它在吐骨头。”齐明月突然冲过去掀开井盖。黑洞洞的井口喷出腐臭味,
她举着手电筒往下照时,光束突然扭曲成螺旋状。有东西在底下反光。
福伯发出“啊啊”的气音,拼命拽我袖子。他另一只手里攥着湿漉漉的铜钱,
钱孔里穿着的红绳正在融化成血水。陈青囊把流血的手按在井沿上。
青苔下浮现出暗红色脉络,像血管一样搏动。包袱里的蓝光突然变成惨绿色,
照得我们四个人的脸像死人。“沈星移。”他第一次叫我全名,“你祖父怎么死的?
”假山上的符咒突然自燃。火苗是绿的。第3章绿火在假山上烧出焦黑的痕迹。
陈青囊的手还按在井沿上,血渗进青苔的脉络里,像某种古老的契约。“我祖父是病死的。
”我盯着他掌心的伤口,“肺痨。”齐明月突然冷笑。她从药箱夹层抽出一张泛黄的病历,
拍在我胸口。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,但“金属中毒”四个字刺得我眼睛发疼。
陈青囊的包袱开始剧烈抖动。他解开结扣的瞬间,井水突然漫上来,打湿了我的布鞋。
河图洛书浮在半空,金色篆文像蝌蚪一样游动,映在井壁上变成锁链的形状。“拼起来。
”他扔给我半面铜镜。镜缘的鸾鸟纹缺了翅膀。我手指刚碰到缺口,就被锋利的铜边划破。
血珠滚进花纹的刹那,井水突然沸腾。福伯发出嘶哑的喉音,扑过来抢铜镜。
老人枯瘦的手指异常有力,指甲抠进我手腕的旧伤——那是祖父去世那夜留下的抓痕。
铜镜落地摔成三瓣。每一块碎片里都映出不同的脸:我流血的手,齐明月苍白的嘴唇,
陈青囊发光的瞳孔。井水漫过青石板,水面浮现出铁锈色的影子。那东西在井底游动,
搅得水波荡出奇特的频率。我太阳穴突突直跳,突然听见金属摩擦的声响。
齐明月药箱里的朱砂符自己飘了出来。黄纸上的咒文正在融化,红液滴在水面上,
立刻被吸进井底。“退后!”陈青囊拽开我。井壁的青砖缝隙里渗出黑雾。
那些雾气聚成爪子的形状,抓住福伯的脚踝就往井下拖。老人拼命挣扎,
铜钱从口袋里哗啦啦往外掉,每一枚落地的声音都像在敲丧钟。我扑过去抓住福伯的胳膊。
触感冰凉滑腻,根本不像是活人的皮肤。陈青囊往我手里塞了块镜片:“照井底!
”水面映出的不再是我们的倒影。一条模糊的龙形被铁链锁在井底,每片鳞甲都在渗血。
那些血珠浮到水面就变成金点,和之前砖缝里的龙血纹一模一样。齐明月突然按住自己脖子。
她雪白的皮肤下浮现出锁链状的红痕,就像井底龙影的缩小版。
陈青囊的河图洛书猛地贴到她背上,金色篆文钻进她衣领。“医师小姐。
”他声音带着古怪的回音,“你每晚梦见的铁索声,就是这个。”福伯终于挣脱黑雾,
瘫在地上剧烈咳嗽。他吐出的黑水里裹着碎铜钱,落地就化成了腥臭的泥。井水突然退去。
青石板上留着几片逆鳞状的湿痕,中间躺着个生锈的铜匣。我弯腰去捡,后颈突然一凉。
有试读30%东西在井底叹气。第4章井底那声叹息还在我后颈上爬,天上突然飘下黑雪。
我伸手接住一片。雪花在掌心化开,留下煤灰般的污渍。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,
戏楼方向腾起浓烟。“日军进城了。”陈青囊掸掉肩上的黑雪,
包袱里的河图洛书发出蜂鸣般的震动,“龙脉在流血。”齐明月突然抓住我胳膊。
她指甲掐进我皮肉,脖子上的锁链红痕已经变成青紫色。
“地质图...”她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“我父亲的书房...”铜匣在我手里发烫。
匣盖上的饕餮纹正一张一合地蠕动,仿佛在咀嚼什么无形的东西。福伯蜷缩在井台边,
把吐出来的铜钱残片排成残缺的星宿图案。陈青囊突然按住我天灵盖。
眼前闪过破碎的画面:地底纵横交错的暗河,每道水流都裹着金红色的血丝。
最深处盘踞着模糊的龙影,七寸位置插着半面铜镜。“镇龙镜缺了阴面。”他松开手时,
我鼻腔里充满铁锈味,“龙脉的伤痛会具象成灾厄。”又一声爆炸。
这次近得震碎后院花窗的玻璃。齐明月白大褂上溅了泥点,她拽着我们冲向洋楼时,
药箱里传来符纸燃烧的焦味。她父亲的书房积满灰尘。
西洋解剖图旁边挂着泛黄的《山海经》拓本,玻璃柜里陈列着各种矿石标本。
最底层的抽屉锁着黄铜密码盘,齐明月转动刻度时,
我注意到她手腕内侧有个和井底龙影一模一样的胎记。“他死前一周画的。
”她展开一卷桑皮纸,七个红圈像血滴般醒目,“龙穴坐标。”陈青囊的包袱突然自动解开。
河图洛书悬浮在图纸上方,金色光点与七个红圈重合了三个。剩下的四个红圈开始渗出墨汁,
在纸上蜿蜒成扭曲的路线。福伯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。老人手里攥着从后院捡来的镜片,
浑浊的眼球死死盯着图纸。他突然发出“嗬嗬”的喉音,枯枝般的手指戳向最远的那个红圈。
戏楼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。窗外的黑雪下得更密了,有几片粘在玻璃上,像腐烂的蛾子。
“广和楼...”我喉咙发紧,“第一个坐标在戏楼底下?”铜匣突然弹开。
里面滚出枚生锈的指南针,指针疯狂旋转后指向戏楼方向。齐明月猛地合上抽屉,
她白大褂口袋里飘出半张烧焦的符纸,灰烬组成“癸水”两个篆字。
陈青囊用锈钉在掌心划了道口子。血滴在图纸上,四个未重合的红圈突然凸起,
变成细小的火山口喷出腥气。“不是戏楼。”他舔掉掌心的血,
“是戏楼地窖里的古井——他们正在龙眼上架机枪。”福伯突然剧烈咳嗽。
他吐出一团缠绕着黑发的铜钱,钱币落地就碎成粉末。老人用最后力气抓起桌上的裁纸刀,
在自己枯瘦的胳膊上刻出歪扭的星图。血珠滴在图纸那刻,
河图洛书上的光点全部变成了黑色。远处传来整齐的皮靴声。
陈青囊迅速卷起图纸塞进我怀里,他的包袱发出警报般的红光:“子时前找到阴面镜,
否则...”院墙外传来日语吆喝声。齐明月突然拉开标本柜,露出后面漆黑的密道。
福伯推我进去时,我瞥见他袖口滑出的铜钱——正在融化成龙鳞状的铜汁。密道门关上那刻,
整个书房突然剧烈摇晃。标本柜里的矿石相互碰撞,发出类似龙吟的共鸣。
黑暗中有东西在呼吸。第5章密道里的呼吸声带着铁锈味。我摸到墙上的苔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