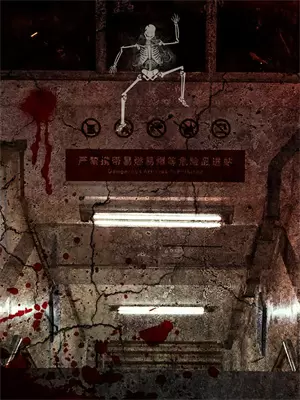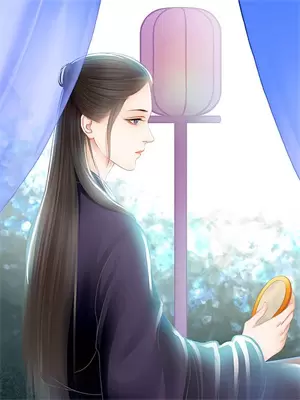我用记忆换他十年,他却骂我疯子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总用奇怪的眼神看我。
直到他拦住我:“你十年前就该死了,为什么还活着?”我愣住了,因为他说的那个日期,
正是我记忆中一场致命车祸的日子。而那天,我本该在车上。
实习生颤抖着说:“那辆车上的二十三人都死了,只有你活下来。”“因为你用未来换来的,
”他盯着我,“你卖掉了未来十年,现在时间到了。”---公司新来了个实习生,叫林晓,
二十出头的年纪,清清秀秀,却总带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郁。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,
不是下属对上级的敬畏,也不是年轻人常见的好奇,那是一种……混杂着探究、恐惧,
甚至是一丝怜悯的复杂注视。每次在茶水间偶遇,或者我走过开放式工位,
总能感到那道黏着的视线,待我回望过去,他又会立刻低下头,假装忙碌,
只留下一个仓皇的侧影。起初我只当是年轻人初入职场的不适应,或者我过于敏感,
并未多想。直到那个加班的深夜。项目收尾,我留在公司核对最后的数据,
偌大的办公区只剩下我敲击键盘的嗒嗒声和中央空调低沉的嗡鸣。起身去接第三杯咖啡时,
才发现林晓的工位还亮着灯,他伏在桌上,像是睡着了。我摇摇头,年轻人拼劲是足,
但也不该这样熬。正准备离开,他却猛地抬起头,眼眶泛红,直勾勾地看向我,
那眼神里再没了白天的闪躲,只剩下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。他站起身,径直走到我面前,
挡住了去路。声音因为紧张而干涩发颤,在寂静的空间里异常清晰:“周哥,你…你十年前,
是不是本该死在5月17号那场车祸里?”我端着咖啡杯的手猛地一僵,
滚烫的液体溅出几滴,落在手背上,带来细微的刺痛。5月17号。
这个日期像一枚生锈的钉子,早已被我用厚厚的时间尘埃掩埋,
此刻却被他不容分说地撬开了一道缝隙。“你怎么知道?”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陌生。
他死死盯着我,嘴唇失去了血色,身体也在微微发抖,
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才继续说下去:“西山线,那辆傍晚出发的长途大巴,
侧翻坠崖…车上连司机带乘客,二十三人,无一幸免。新闻报了,名单也有……那上面,
本来应该有你的名字。”记忆的闸门被强行冲开,腥锈的洪水呼啸而至。那天,
我确实该在那辆车上。已经买好了票,准备去邻市处理一件紧急的家事。
甚至连靠窗的位置都提前选好了。可临出发前,
我鬼使神差地接了一个极其无聊、耗时不短的推销电话,错过了发车时间。
等我气急败坏地赶到车站,只能眼睁睁看着那辆大巴驶出站台。几个小时后,
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了那起惨烈事故的新闻。劫后余生的庆幸持续了没多久,
就被一种巨大的虚无所取代。那感觉不像幸运,更像是一种…误差。仿佛命运的账簿上,
某个数字被临时涂改了一下。“你本来该死在那里的。”林晓的声音更低了,
带着一种诡异的确认感,“你为什么还活着?”我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比如只是运气好,
错过了而已。但看着他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,所有敷衍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。
他往前凑了半步,声音压得极低,却像惊雷一样在我耳边炸开:“因为你用未来换的。
”“什么?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“你卖掉了你的未来十年,”他一字一顿,
每个字都清晰无比,带着冰冷的重量砸向我,“换来了那次‘错过’。现在,周哥,
时间到了。”时间到了。三个字,像三把冰锥,瞬间刺穿了我十年的伪装。
那些被我刻意忽略的细节,此刻争先恐后地涌上心头——这几年,身体似乎没什么大病,
但精力总是不济,对什么都提不起太大兴趣,仿佛生活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偶尔会有几秒钟莫名其妙的恍惚,好像意识短暂地脱离了一下身体。还有,
关于那场车祸前的记忆,有些部分确实模糊得厉害,尤其是错过班车前的那一小段时间,
完全想不起具体细节,只记得一个漫长的、令人烦躁的通话。我一直以为,
那只是创伤后应激,或是人到中年的常态。冷汗,无声无息地从背脊渗了出来,
迅速浸湿了衬衫。咖啡杯在我手中不受控制地晃动,发出咔哒的轻响。
“你…你到底在胡说什么?”我试图维持最后一丝镇定,声音却出卖了我,带着明显的裂隙。
林晓没有回答,只是用一种混合着悲伤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,然后,他猛地转身,
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办公区,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,浑身冰冷。那一夜,我彻夜未眠。
林晓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。“卖掉未来”、“时间到了”。荒谬,
绝顶的荒谬!这一定是某种恶作剧,或者那孩子精神出了问题。可他那时的眼神,
他话语里那种不容置疑的细节——具体的日期、班车线路、死亡人数……一个实习生,
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?那起事故虽然上了新闻,但早已被公众遗忘,除非特意去查旧档案。
接下来的几天,公司一切如常。项目顺利结束,我还得到了上司的表扬。但一切都不同了。
我看似坐在工位上处理邮件,参与会议,和同事谈笑风生,但灵魂像是飘在了半空,
冷眼旁观着另一个叫“周正”的人在进行这一切表演。林晓请了病假,没来上班。
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安。我必须弄清楚。趁着午休,我把自己反锁在狭小的防火楼梯间,
用手机开始搜索。关键词:“西山线 5月17日 车祸”。十年过去了,
网络上的信息残留不多,只有几条当年地方新闻的转载快照,点进去图片大多已失效。
文字描述和林晓说的基本一致:事故,二十三人遇难。我深吸一口气,
开始尝试搜索遇难者名单。这更困难,翻了十几页,
才在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地方论坛的悼念帖里,找到一个粘贴的名单截图。像素很低,
名字密密麻麻。我的手指有些发抖,慢慢向下滑动。然后,我的呼吸停滞了。
在名单的中间偏后位置,我看到了两个字。周正。白底黑字,模糊,但绝不会错。我的名字,
赫然列在十年前那场车祸的遇难者名单上。一股寒气从脚底瞬间窜上天灵盖,
手机差点脱手滑落。我猛地靠在冰冷的墙壁上,才勉强支撑住发软的身体。这不可能!
一定是重名!中国那么大,叫周正的人太多了!我试图这样告诉自己,
可心底有一个声音在尖叫:时间、地点、班次……所有线索都严丝合缝地对上了!
这就是我本该乘坐的那辆车!那我是谁?这十年来,活着的是谁?浑浑噩噩地回到工位,
整个下午我都无法集中精神。眼前屏幕上的字符在跳动,
同事们交谈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层水传来,模糊不清。那个名单上的“周正”两个字,
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视网膜上。快下班时,内线电话突然响了。我接起来,是前台,
说有一位姓陈的女士找我,没有预约。我木然地走到前台,
看到一个穿着朴素、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等在那里,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陈旧的帆布包。
她看到我,眼神先是确认,随即涌上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,像是憎恶,又像是恐惧,
还夹杂着一丝绝望。“你是周正?”她问,声音沙哑。“我是。您是?”“陈萍。
”她报出一个名字,见我毫无反应,她扯了扯嘴角,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,
“你果然不记得了。我丈夫,李建国,十年前,和你坐的同一班车。”李建国?
我努力在记忆里搜寻,一片空白。“他死了。”陈萍死死盯着我,“你没死。”我喉咙发干,
不知该如何回应。“十年了……我一直想不通,为什么是你活下来?”她的声音开始颤抖,
“名单上有你,现场…现场据说很惨,别人都…都找到了,唯独没有你。
你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,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活着!”“陈女士,
我想你误会了……”我试图解释,却苍白无力。“误会?”她猛地打断我,
从那个旧帆布包里掏出一张塑封好的、边角磨损严重的照片,几乎是戳到我眼前,“你看!
这是出发前,在车站,我给他们父子拍的!你看背景!角落里那个看表的!是不是你?!
”照片像素不高,背景杂乱,但在人群的边缘,
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、低头看手腕的年轻侧影,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。那是我。十年前的我。
那个本该在几分钟后登上死亡班车的我。巨大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,扼住了我的喉咙。
我盯着那个侧影,关于那天的、一直模糊不清的记忆碎片,似乎松动了一下,
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茫然和惊骇。“你用什么换的命?”陈萍逼近一步,眼神锐利得像刀,
“啊?你告诉我!你凭什么活下来?!我的丈夫,我的儿子…他们都没了!
你为什么能好好站在这里?!”她的声音引来了周遭同事侧目,但她浑然不顾。
保安闻讯赶来,客气但强硬地将情绪激动的陈萍请走了。她被带走时,还回头死死瞪着我,
那眼神里的恨意和绝望,让我如坠冰窟。她的话,和那张照片,像最后两块拼图,
彻底击碎了我所有的侥幸。林晓说的,很可能是真的。我必须找到林晓。
我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方式找他。打电话,关机。发邮件,石沉大海。问他同组的同事,
只说他请假了,原因不详。我甚至找到了他入职时填写的紧急联系人电话,打过去,
是他老家一个远房亲戚,说他很久没和家里联系了,也不知道他现在具体的住址。
就在我一筹莫展,几乎要放弃的时候,我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。没有标题,没有正文,
只有一个附件,是一个加密的压缩包。密码提示问题很简单:“你记忆的起点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