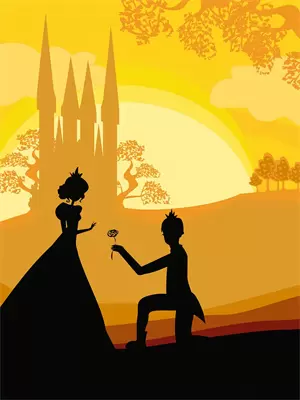1相识又分别陈砚第一次见到苏野,是在二十岁的深秋。
那天他抱着刚从图书馆借来的古籍,在文学院后门的银杏道上走,风卷着金黄的叶子扑过来,
他没站稳,怀里的书哗啦啦散了一地。正蹲下来捡时,一双穿着白色板鞋的脚停在他面前,
下一秒,骨节分明的手就帮他拾起了最底下那本《昭明文选》。“小心点,
这书的封皮都快掉了。”那人声音很亮,像碎冰撞在玻璃上,陈砚抬头,
看见个穿焦糖色卫衣的男生,头发微卷,额前碎发被风吹得晃,
笑起来时左边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,“我叫苏野,新闻系的,你呢?”“陈砚,历史系。
”陈砚的声音有点闷,他接过书,指尖不小心碰到苏野的手背,对方的温度比他高些,
像揣了颗小太阳,“谢谢。”那之后他们总在校园里遇见。苏野像是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,
会在早上冲进食堂时朝他挥手,喊“陈砚,帮我占个座”;会在傍晚的篮球场边,
举着两瓶冰可乐跑过来,把其中一瓶塞给他,说“刚赢了比赛,
请客”;还会在图书馆闭馆后,陪他走回宿舍,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
苏野会絮絮叨叨说今天采访遇到的趣事,陈砚就听着,偶尔应一声,心里却像被温水泡过,
软乎乎的。陈砚性子静,不爱说话,苏野却偏能看透他的心思。有次陈砚因为论文选题烦躁,
在银杏道上坐了一下午,苏野找到他时,手里拿着个烤红薯,还冒着热气。
“我猜你没吃晚饭。”苏野把红薯递给他,自己也坐下来,“选题的事别急,
你不是喜欢明清史吗?不如从《万历起居注》入手,我帮你找资料。”那天的红薯很甜,
暖得陈砚手指都不凉了。他看着苏野认真分析选题的侧脸,突然觉得,
深秋的风好像也没那么冷了。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,形影不离。
苏野的相机里全是陈砚的照片:在图书馆看书的、在银杏道上走的、甚至是蹲在路边喂猫的,
每张照片里,陈砚的眼神都很软,连带着周围的风景都温柔起来。苏野总说:“陈砚,
你长得好看,就该多拍点照。”陈砚不反驳,只是在苏野摆弄相机时,
悄悄把他的样子刻进心里。大三那年冬天,学校举办跨院系晚会,苏野拉着陈砚报了节目,
唱《南方姑娘》。彩排时苏野总忘词,陈砚就耐心地帮他记,两人凑在一张乐谱前,
呼吸交缠,陈砚能闻到苏野身上淡淡的柑橘味,心跳得像要撞开胸腔。晚会那天,
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,苏野唱到“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”时,
突然转头看向陈砚,眼神亮得惊人。陈砚愣了一下,随即笑起来,跟着他一起唱。
台下掌声雷动,陈砚却只看得见苏野的眼睛,像盛着漫天星光。晚会结束后,
他们在操场散步,雪轻轻落下来,落在苏野的头发上,像撒了把碎糖。苏野突然停下来,
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盒子,递给陈砚:“给你的,生日礼物。”那天是陈砚的生日,
他自己都忘了。他打开盒子,里面是一枚银质的书签,刻着“砚”字,
边缘还缀着个小小的银杏叶吊坠。“我自己做的,有点丑。”苏野挠了挠头,耳朵有点红。
“很好看,”陈砚的声音有点发颤,他握紧书签,“苏野,谢谢你。”“谢什么,
”苏野笑起来,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,“我们是朋友啊。”朋友。这两个字像根细针,
轻轻扎在陈砚心上,有点疼,却又不敢说出口。他知道苏野家境不好,母亲常年生病,
他课余时间要做兼职、拍照片挣钱,却从来没在他面前抱怨过。陈砚想帮他,
却又怕伤了他的自尊,只能默默陪他,在他熬夜赶稿时递杯热牛奶,在他兼职回来晚时,
在宿舍楼下等他。大四那年春天,苏野拿到了一家北京媒体的实习机会,要提前去报道。
出发前一天,他们在银杏道上走了很久,苏野说:“陈砚,等我实习结束,
就回来陪你写毕业论文,我们还要一起去爬泰山,看日出。”陈砚点头,喉咙发紧,
说不出话。他看着苏野,想说“我喜欢你”,想说“你别去北京”,
可最后只变成一句“路上小心”。苏野走的那天,陈砚没去送。他躲在宿舍里,
看着苏野送他的书签,眼泪无声地掉下来。他知道,苏野就像风,永远不会停在一个地方,
而他,只能站在原地,等着风回来。苏野去北京后,他们每天都通电话。
苏野会说实习的趣事,说北京的胡同很好看,
说等他回来带陈砚去吃烤鸭;陈砚会说学校的事,说他的论文有了进展,
说银杏道的叶子又绿了。他们的电话总能聊很久,直到手机发烫,才恋恋不舍地挂掉。
可渐渐地,苏野的电话越来越少,回复消息也越来越慢。陈砚安慰自己,他只是太忙了,
却还是忍不住担心,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,盯着手机屏幕等消息。有天晚上,
陈砚终于接到了苏野的电话,可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虚弱,还带着咳嗽。“陈砚,
”苏野的声音很轻,“我有点不舒服,可能最近不能给你打电话了。”“你怎么了?
是不是生病了?”陈砚急了,“要不要我去北京看你?”“不用,”苏野笑了笑,
声音却很哑,“就是小感冒,过几天就好了。你别担心,好好写论文。”挂了电话,
陈砚的心一直悬着。他想去找苏野,可又怕打扰他。他只能每天给苏野发消息,说学校的事,
说他今天吃了什么,即使苏野很少回复,他也没停过。毕业答辩那天,陈砚拿到了优秀论文,
他第一时间想告诉苏野,却发现还是联系不上他。他去问苏野的室友,室友犹豫了很久,
才说:“苏野……他早就不在北京了,他妈妈病重,他回了老家,还退学了。”陈砚愣住了,
像被人泼了盆冷水,从头凉到脚。他疯了一样给苏野打电话,发消息,可都石沉大海。
他去苏野的老家找过,可苏野的邻居说,他们早就搬走了,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陈砚毕业了,
他没有去读研,而是留在了学校所在的城市,找了份古籍修复的工作。
他还住在原来的宿舍附近,每天都会去银杏道上走一圈,就像苏野还在的时候一样。
他把苏野送他的书签一直带在身边,看书时用它,写字时也把它放在手边,
仿佛苏野还在他身边,陪着他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陈砚身边也有过追求者,可他都拒绝了。
他心里的位置,早就被那个穿焦糖色卫衣、笑起来有梨涡的男生占满了,再也容不下别人。
五年后的一个深秋,陈砚去外地参加古籍研讨会,在当地的博物馆里,他看到了一个摄影展,
主题是“故乡的风”。他本来没打算看,可当他看到第一张照片时,
脚步却停住了——照片里是个穿焦糖色卫衣的男生,站在银杏道上,
笑起来左边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,背景里,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正抱着书走过来,侧脸温柔。
那是他们大三那年,苏野拍的照片。陈砚的心跳得飞快,他沿着展台一直走,
里的场景越来越熟悉:图书馆的靠窗座位、操场的篮球场、宿舍楼下的路灯……每张照片里,
都有他的影子,有的清晰,有的模糊,却都被拍得很温柔。最后一张照片前,
放着一个笔记本,旁边有个说明:“此笔记本为摄影师苏野遗物,
生前希望若有人认出照片中的人,可将笔记本转交。”陈砚的手颤抖着,翻开笔记本,
里面全是苏野的字迹,从他去北京那天开始写起——“今天离开的时候,没敢让陈砚送,
我怕看到他的眼睛,就舍不得走了。他还不知道,我喜欢他,
从第一次在银杏道上帮他捡书的时候,就喜欢了。”“北京的实习很累,每天要跑很多地方,
可只要想到陈砚,就觉得有动力了。我得好好挣钱,等攒够了钱,就回去跟他表白,
跟他一起去爬泰山,看日出。”“妈又住院了,医生说情况不太好,需要很多钱。
我跟公司辞了职,回了老家。我不能告诉陈砚,我怕他担心,怕拖累他。他那么优秀,
应该有更好的未来,而不是跟我一起吃苦。”“最近身体越来越差,咳嗽得厉害,
医生说我得了肺癌,跟我爸一样的病。也好,这样就不用再纠结要不要跟陈砚说了,
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,我想在他心里,永远是那个能跑能跳、笑起来有梨涡的苏野。
”“今天拍了张照片,是故乡的银杏道,跟学校的很像。
我想起以前跟陈砚一起在银杏道上走的日子,真怀念啊。如果有下辈子,
我一定要早点跟他表白,跟他一起过一辈子,再也不分开。”“陈砚,
我好像等不到回去跟你说‘我喜欢你’了。对不起,让你等了这么久。你一定要好好的,
找个喜欢的人,过幸福的日子,别再想起我了。”笔记本的最后一页,夹着一封信,
信封上写着“致陈砚”,邮票没贴,地址也没写,显然,这封信从来没寄出去过。
陈砚拆开信,里面只有一张纸,上面是苏野熟悉的字迹,只有一句话:“陈砚,
银杏道的叶子又黄了,我好想你,好想再跟你一起走一次。”陈砚蹲在展台前,
抱着笔记本哭得撕心裂肺。周围的人都在看他,可他不在乎,他只知道,
那个他等了五年、想了五年的人,再也不会回来了;那个说要陪他去爬泰山、看日出的人,
永远停在了那个深秋;那个喜欢他的人,把爱意藏在照片里、笔记本里,藏了一辈子,
却从来没说出口。研讨会结束后,陈砚把苏野的笔记本和信带回了家。
他还是每天去银杏道上走一圈,只是现在,他会带着笔记本,把苏野写的话读给风听,
就像苏野还在他身边,听他说话一样。每年深秋,银杏叶黄的时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