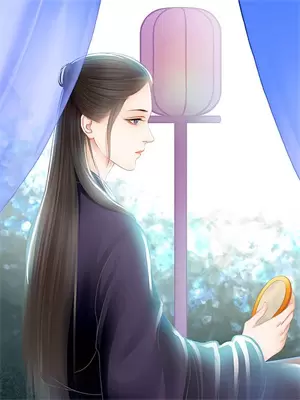第一章:琥珀圣玛丽亚心理康复中心坐落在远离市区的山坳里,
灰白色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群像一群沉默的巨兽,匍匐在终年不散的雾气中。
这里的宣传语写着:“在圣玛丽亚,我们陪您梳理心灵褶皱,找回内在的平和与秩序。
”官方绝不会提及,所谓“梳理褶皱”,
依赖的是一种代号“琥珀”的情绪调节制剂——它会通过每日餐食、空气净化系统,
甚至“康复辅导”,悄然融入使用者体内。最终,人会慢慢失去剧烈欢笑的雀跃,
也失去放声痛哭的冲动,变得温顺、平和,符合这里“标准化康复”的要求。我叫苏晚,
编号734,是这里的“特殊案例”。“琥珀”对我效果微弱。
恐惧时的心跳加速、悲伤时的眼眶酸涩、愤怒时的胸腔灼痛,这些本应被“抚平”的情绪,
仍像顽固的藤蔓,在我心底疯长。这在中心里是“康复倒退”的信号,
意味着要增加“治疗”强度,直到我彻底符合“标准”。我必须藏好这份“特殊”,
像守护一个不能见光的秘密。午餐时,食堂静得只剩餐具轻碰的声响。每个人都安静咀嚼,
脸上是千篇一律的平和,仿佛被精心打磨过。我低着头,小口吃着餐盘里的营养餐,
指尖控制不住地发颤——今天餐食里“琥珀”的剂量,似乎比往常重,甜腻感堵在喉咙口,
让我阵阵反胃。突然,对面传来“哐当”一声脆响。是顾衍之,编号809。
他的餐盘翻在地上,营养餐溅了一地,可他依旧坐得笔直,面无表情,桌下的手却指节泛白,
微微颤抖。周围人连眼皮都没抬,只有几位穿白大褂、臂章印着“康复助理”的工作人员,
目光锐利地扫过来。“809号,情绪波动异常,记录。下午追加一次舒缓辅导。
”冰冷的声音响起。顾衍之没反应,只是缓缓松开拳头,任由工作人员带离食堂。我知道,
他不是失控——他在“感知”。他对“琥珀”的浓度格外敏感,一旦超过临界值,
身体会先于意识产生排斥,打翻餐盘,是他偷偷预警的方式。而我的眼泪,
就是另一种“感知器”。哪怕是微量“琥珀”,也会让我的泪腺产生反应。
我们是这座“标准康复园”里,彼此心照不宣的“感知者”。
第二章:暗流圣玛丽亚并非铁板一块,这里的人大致分几类。一类是像李主任这样的管理者,
精明且严谨,是“琥珀”调节体系的执行者,
把所有“情绪波动”都视作需要修正的问题;一类是普通医护,大多按部就班,
比如总带着倦容的护士张姐,话不多,只做好本职工作;还有一类,
是像陈医生这样的年轻人。陈医生负责我的“心理辅导”,戴金丝边眼镜,说话温和,
总试着引导我“接纳平和”。但有一次,他转身整理资料时,
我瞥见他眼底闪过一丝焦虑——那焦虑和这里的“标准氛围”格格不入,像一颗错位的石子。
此外,还有个特殊的病人,编号110的老周。他在这儿待了最久,平时总喃喃自语,
没人听得懂,大家都觉得他是“康复失败的典型”。可上周,
我在图书馆角落捡到一张他遗落的纸片,上面用细笔勾勒着复杂的线路图,
工整得不像痴呆者的手笔。我和顾衍之,在这样的环境里,
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共生关系——没有熟络的友谊,只有基于“活下去”的相互提醒。放风时,
我们会躲在监控死角的废弃花房,用无声的方式交流。
他会在泥土上划符号:叉代表某份餐食剂量异常,圈代表空气里“琥珀”浓度偏高;偶尔,
他还会带来“干净”的东西——一小块没加制剂的苹果,
或是旧书里描写“正常情绪”的残页。作为回报,
我会告诉他我的“感知”:今天的温水喝着发涩,
肯定掺了制剂;新来的助理身上有特殊香氛,底下藏着高浓度“琥珀”挥发剂。
我们像两只在黑暗里摸索的动物,靠彼此的“特殊”确认自己还“正常”,
也一点点拼凑着这座中心的真相。第三章:裂隙中心的“平和”,
被一个叫小雅的女孩打破了。小雅才十几岁,据说因为“情绪起伏过大”后来我才知道,
是和同学闹了矛盾,被家人送来。她还没被“琥珀”彻底影响,眼里藏着恐惧,
走路时会悄悄躲着工作人员。或许是这份“不配合”,工作人员对她格外严格。一天深夜,
我隐约听到隔壁传来压抑的哭声,还有轻微的挣扎声——是小雅。
紧接着是工作人员的低声叮嘱,还有仪器启动的嗡鸣。第二天再见到小雅,她眼里的光没了,
走路僵硬,脸上只剩和其他人一样的“平和”。一股寒意,在我和顾衍之之间悄悄蔓延。
那天在花房,他没划符号,只是用拳头砸向斑驳的墙壁,指节磕出了血。而我,
第一次没接触“琥珀”,也流下了眼泪——为小雅,也为我们看不清的未来。
陈医生似乎也察觉到了异常。一次辅导时,他看似无意地说:“最近中心调整了一些流程,
你们尽量配合,别给自己添麻烦。”语气里,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提醒。老周还是老样子,
疯疯癫癫地晃悠。但有次擦肩而过时,他突然塞给我一个纸团,展开一看,上面画着个箭头,
指向中心地下室的方向。线索零碎,却都透着危险。我和顾衍之都明白,
圣玛丽亚不只是“康复中心”,“琥珀”背后,肯定藏着更多事。而小雅的遭遇提醒我们,
这里的“标准”正在收紧,我们没多少时间了。第四章:深潭我们决定去地下室看看。
趁一次电路检修、监控暂时失灵的间隙,顾衍之用不知道从哪儿学的技巧,
撬开了地下室的门锁。门一开,里面的景象让我们浑身发僵——这不是储物间,
是个小型实验室。冰冷的仪器屏幕上跳着数据,柜子里摆着各种颜色的试剂,
比给我们用的“琥珀”复杂得多。更关键的是,我们找到了几箱档案。档案里写着,
圣玛丽亚是“情绪调节试点项目”的一部分。“琥珀”的目的,不只是“帮助康复”,
而是要测试“标准化情绪管理”的可行性,为后续推广积累数据。我们这些“病人”,
其实是项目的“观察对象”;像小雅这样“不配合”的,会被进行“深度辅导”,
确保符合“标准”。还有一份加密名单,上面除了我们,竟然还有陈医生的名字!
备注写着:“潜在共情倾向,需持续观察,暂不调整干预方案。”原来,
陈医生不是“执行者”,他也是被观察的人,只是没被拆穿。最让我们震惊的,
是一份泛黄的记录。上面写着,我和顾衍之不是“偶然对琥珀敏感”——我们的父母,
是早期“情绪调节试剂测试”的志愿者,在接受测试后生下了我们。我们对“琥珀”的抗性,
是遗传带来的反应。而记录末尾,父母的状态都标着“测试结束,终止随访”。真相像冰锥,
扎进心里。我们不是“特殊案例”,是测试的“副产品”,从出生起,
就被打上了“需要观察”的标签。就在我们攥着档案想离开时,地下室的门突然被撞开。
李主任带着几个穿安保服的人站在门口,脸上挂着冷笑。“果然,两个‘观察异常者’,
还是找过来了。”李主任的声音发沉,“看来普通‘琥珀’对你们没用了,
得换种‘干预方式’,确保你们符合标准。”第五章:决堤我们被拖到了中心的天台。
风很大,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。李主任说,要“处理”我们,再伪装成“康复期情绪失控,
意外坠楼”。安保人员步步紧逼,手里的电击棍闪着蓝光。顾衍之突然笑了,不是害怕,
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。他看向我,眼里映着天台的冷风,还有我发白的脸。
“他们不是要‘绝对平和’吗?”他的声音被风吹得发飘,却很清楚。没等我反应,
他突然把我拉近,低头吻了我。那不是温柔的吻,带着点慌乱,甚至咬破了彼此的嘴唇,
血腥味在舌尖散开。愤怒、委屈、对“标准”的反抗、对“正常”的渴望,
所有被压抑的情绪,都在这一刻涌了出来。我没推开他,反而攥着他的衣服,
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——不是疼,是终于不用再藏情绪的释放。几乎同时,
中心的警报突然响了,不是火警,是尖锐的“异常情绪监测警报”!
李主任和安保人员手腕上的监测仪瞬间爆红,数据疯狂跳动,几乎要溢出屏幕。
楼下的“病人”们,也开始骚动,有人停下脚步,
有人下意识摸了摸胸口——这些“平和”的反应,在以前从未有过。广播里传来电子音,
带着一丝卡顿:“警报!检测到极端情绪波动!坐标天台!个体809,愉悦指数96%,
愤怒指数98%!个体734,悲伤指数97%,共情指数99%!波动超出安全阈值,
系统无法定义!启动……启动临时应对方案……”李主任的脸色变了,
慌乱地喊着“控制住他们”,可监测仪的警报声,盖过了他的指令。顾衍之松开我,
唇边沾着血,看着楼下的骚动,眼里的压抑终于散了。我的眼泪砸在天台的水泥地上,
烫得像火。“标准”的裂缝,从我们身上,蔓延到了整个中心。混乱中,
我看到陈医生冲上天台,身后跟着护士张姐,还有几个平时沉默的医护——他们眼里,
没了往日的麻木。而远处的角落,老周靠在墙上,不再喃喃自语,手里拿着个小装置,
眼神清醒得吓人。风暴才刚开始。我们的反抗,只是撕开了真相的一角,
真实想法、父母当年的测试真相、“琥珀”项目的真正目的……这不再是“躲起来活下去”,
而是要找回“不用伪装情绪”的权利。第六章:火种天台的警报,像一把锤子,
砸碎了圣玛丽亚的“平和”假象。楼下的“病人”们,在警报声和情绪波动的影响下,
不再机械地走动——有人茫然地看着四周,有人用手捂住耳朵,甚至有人轻声啜泣,
这些“不标准”的反应,以前从未出现过。“系统无法定义!情绪波动范围扩大!
”广播里的电子音,还在重复着混乱的指令。李主任的脸铁青,对着通讯器吼着,
却被杂音盖过,只能冲身边的安保喊:“抓住他们!别让他们跑了!
”可安保人员盯着手腕上爆红的监测仪,眼神里多了点犹豫——他们习惯了“标准情绪”,
从没见过这么剧烈、无法定义的波动,这种“未知”,打破了他们的本能服从。
就是这几秒的犹豫,陈医生已经冲到我们面前,挡住了安保的路。张姐跟在后面,
手里拿着个灭火器,眼神坚定。“李主任,别再继续了!”陈医生的声音发颤,却很有力,
“你看楼下,这就是你要的‘平和’吗?系统已经乱了,再下去,只会更糟!”“陈明!
你果然也是‘异常者’!”李主任眼里冒火,“把他们都拿下!”顾衍之抹掉唇边的血,
突然踢起脚边的空水桶,砸向逼近的安保,制造出更多混乱。他拉着我的手,低声说:“走!
消防梯!”我们没走楼梯口——那里肯定被堵了,而是冲向天台另一侧的维修消防梯。
陈医生和张姐故意挡在安保前面,给我们争取时间。刚跑到消防梯旁,
老周突然从天台入口的阴影里走出来。他手里拿着个巴掌大的装置,冲我们点了点头,
按下了一个按钮。“滋啦——”中心的灯光突然闪了几下,天台和楼下几层的灯,直接灭了!
黑暗里,安保的脚步声和呵斥声,瞬间乱了。是老周!他切断了部分电源!我们没时间惊讶,
抓着锈迹斑斑的消防梯往下爬。冷风灌进衣服里,手心被铁梯硌得生疼,
可没人敢停——身后的追兵,还在黑暗里摸索着往下赶。“跟着我,别踩空!
”顾衍之的声音在黑暗里很稳。他好像对中心的地形格外熟悉,爬到底后,
没往大门跑那里肯定有安保,而是绕到建筑群后面,钻进了藤蔓掩盖的通风管道入口。
“这里能通到中心外的树林,老周以前跟我说过。”他边爬边解释,声音里带着点喘息。
管道里又黑又潮,满是灰尘味。我们爬了十几分钟,终于看到了出口的光亮。推开栅格,
新鲜的空气涌进来,外面是中心围墙外的树林——我们逃出来了!
第七章:地下脉络躲在树林里,我们终于敢大口喘气。远处,中心的警报声还隐约能听到,
却越来越远,暂时安全了。“老周……他怎么办?”我喘着气问,还有陈医生和张姐,
他们留在里面,肯定会被李主任针对。顾衍之靠在树上,脸色还没恢复,
却很冷静:“老周不是真的痴呆,他以前是电气工程师,被送来前,
就研究过中心的电路系统,他肯定有退路。陈医生……我观察他很久了,
他妹妹几年前被送来,后来‘康复出院’,就再也没消息,他来这里,是为了查妹妹的事。
”我愣住了——原来这座“牢笼”里,早就有人在悄悄反抗,我们的爆发,只是点燃了火种。
“我们现在去哪?直接跑远吗?”我问。“不行。”顾衍之摇头,
“李主任肯定已经封锁了附近的路,还会对外说我们‘康复期失控出逃,有潜在风险’,
跑远了,反而容易被发现。而且,我们手里的档案,只是一部分,得找到完整的证据,
让更多人知道圣玛丽亚的事,不然,还会有下一个小雅,下一个‘观察对象’。”他说的对,
只靠我们逃出来,没用,得让“琥珀”项目的真相曝光,
才能彻底结束这种“伪装情绪”的日子。就在这时,
我的口袋里突然震动了一下——是之前老周塞给我的纸团里,藏着的一个迷你传呼机,
一直没敢拿出来,没想到现在响了。打开一看,上面只有一行字:“旧城区,老李电器维修,
安全。”是老周的指引!顾衍之看了一眼,点了点头:“旧城区鱼龙混杂,监控少,
适合暂时躲着。而且,维修铺这种地方,容易藏东西,也方便打听消息。”我们昼伏夜出,
避开大路和监控,靠树林里的野果和溪水充饥,走了两天,终于到了旧城区。
这里的房子又旧又密,街上满是小铺子,和圣玛丽亚的“整齐”完全不一样,
反而让人觉得踏实。按照地址,我们找到了“老李电器维修”。铺面很小,卷帘门半拉着,
里面坐着个戴厚眼镜的老头,正修着旧收音机。我们刚靠近,老头就抬起头,
眼神锐利地扫了我们一眼,没说话,只是侧身让我们进去,然后拉下卷帘门,锁好。
“老周让你们来的?”老头开口,声音沙哑。顾衍之点头,
从口袋里拿出那半张写着地下室箭头的纸,递了过去。老头看了看纸,又看了看我们,
叹了口气:“我叫李振邦,跟老周是老伙计。他早就跟我说过,
中心里有两个‘对琥珀敏感’的孩子,让我多留意,没想到你们真能逃出来。
”他挪开身后的旧书架,后面竟然有个楼梯,通往下地下室。“下面安全,有吃的,
还有电脑。你们先休息,等会儿,把在中心看到的、找到的,都跟我说清楚——老周说,
你们手里的东西,能揭穿‘琥珀’的真相。”我们跟着李振邦下了地下室,
里面比想象中宽敞,有床铺、食物,还有几台电脑,墙上贴满了旧报纸和线路图。
“这里是我平时捣鼓设备、打听消息的地方,没人知道。”李振邦给我们倒了杯热水,
“你们先歇着,晚上我们再慢慢说,现在得先确认老周和陈医生的情况——他们留在里面,
危险得很。”手里的热水,暖了手心,也暖了心里的慌。我们终于有了暂时的落脚点,
也终于有了能信任的人。但我们都明白,这只是暂时的——李主任不会善罢甘休,
“琥珀”项目的背后,还有更大的网,我们要做的,就是找到这张网的线头,把它彻底扯断。
第八章:核心密室休息了一下午,天色暗下来后,李振邦打开了电脑,连接上加密网络,
开始尝试联系老周和陈医生。“老周在中心里装了微型信号发射器,平时藏在身上,
只要没被发现,就能发简单的消息。”李振邦盯着屏幕,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,
“陈医生那边,我之前留过一个加密通讯的备用渠道,就怕出事,现在试试能不能连上。
”屏幕上的信号条一直跳着,忽强忽弱,看得我心都悬着。顾衍之坐在旁边,
手里攥着从中心带出来的那页档案——上面有我们父母的名字,指节因为用力,泛着白。
大概过了十分钟,屏幕突然弹出一条简短的消息,只有几个字母和数字:“周:安,陈:转,
备:B7。”“老周安全!”李振邦松了口气,“陈医生转移了,应该是躲起来了,
‘备:B7’,指的是中心地下室B7区——那里是核心资料室,之前你们没找到,
老周是想让我们想办法拿里面的资料,那才是‘琥珀’项目的核心。
”顾衍之猛地抬头:“我去。”“不行!”我和李振邦同时开口。“现在中心肯定戒严了,
B7区又是核心,你去了就是送上门。”李振邦摇头,“而且我们不知道B7区的安保情况,
连门怎么进都不清楚,不能瞎闯。”顾衍之没反驳,只是看着屏幕上“B7”两个字,
声音低沉:“里面的资料,可能有我父母当年的完整测试记录,还有陈医生妹妹的消息,
不能放着不管。”我懂他的心思——我们都想知道,父母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,
那些“终止随访”的背后,是不是还有更多隐情。李振邦沉默了一会儿,
叹了口气:“去可以,但得等机会,还得做准备。我先查中心现在的安保部署,
老周那边应该能传更多消息过来;另外,我得给你们弄两套新身份,还有防身的东西,
不能再像现在这样,一出门就怕被认出来。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们就在地下室里等消息。
李振邦每天都在电脑前忙活,偶尔出去一趟,回来时会带些吃的,
还有改装过的微型手电筒、信号器——能在紧急情况下发求救信号,
还不会被普通设备检测到。我和顾衍之则跟着李振邦学简单的反侦察技巧,
比如怎么避开监控、怎么识别跟踪的人,还有怎么用那些改装设备。顾衍之学得很快,
甚至还跟着李振邦学了点撬锁、修简单电路的技巧,说是“以防万一”。第三天晚上,
老周又发来消息,这次更详细:“中心安保:白天3班巡逻,晚上2班,
凌晨1点到3点是换班间隙,安保最少;B7区门:指纹+密码,密码每周换,
这周是618942,指纹可以用李主任的——老周藏了个李主任的指纹膜,
在废弃花房的砖缝里;里面有核心硬盘,拿到后立刻走,别多待。
”“指纹膜、密码、安保间隙,都齐了。”李振邦看着消息,眼神凝重,“机会来了,
但风险还是大,凌晨1点到3点,只有2小时,一旦出问题,连退路都没有。
”“我和顾衍之一起去。”我开口,“他负责拿资料,我负责望风,互相有个照应。